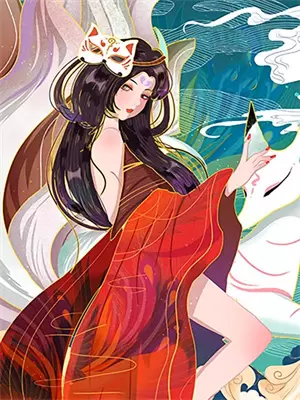电话那头传来妈妈微弱而急促的呼吸声.'救护车...还没来...'她断断续续地说着.我看着时钟秒针每走一圈希望就减少一分.为什么?为什么120永远堵在路上?
电话那头传来妈妈微弱而急促的呼吸声。"救护车...还没来..."她断断续续地说着。我看着时钟秒针每走一圈希望就减少一分。为什么?为什么120永远堵在路上?
"妈,坚持住!我已经打了三次电话了,他们说马上就到!"我的声音在颤抖,手指死死攥着手机,指节发白。
程远,29岁,某金融机构分析师,此刻正经历人生最漫长的72分钟。他站在公司32楼的落地窗前,看着楼下拥堵的车流,第一次感到这座城市的交通网络如此令人绝望。
"小远...我胸口...好疼..."母亲的声音越来越弱,背景里是电视机嘈杂的广告声,那台老旧的松下电视她总舍不得换。
"妈!别挂电话!跟我说话!"我抓起西装外套冲向电梯,同时用另一部手机叫网约车。电梯从1楼缓慢上升,每一秒都像在凌迟我的神经。
"程先生,您母亲的求救电话我们已经收到,最近的救护车正在赶往现场,预计15分钟内到达。"120调度员第三次重复同样的官方说辞,声音机械得令人发指。
"15分钟?45分钟前你们就这么说!我妈有心脏病史,她需要立刻就医!"我的吼声在电梯里回荡,几个同事尴尬地别过脸去。
网约车显示还有8分钟到达。我冲出写字楼,五月的阳光刺得眼睛生疼。手机那头,母亲的喘息声变得断断续续。
"妈!我马上到家!坚持住!"
"小远...妈妈...可能..."
"别说了!保存体力!救护车马上就到!"我钻进网约车,甩给司机五百块钱,"师傅,锦绣花园,闯红灯算我的!"
车子在车流中穿梭,我死死盯着手机上的导航。12公里,正常情况下25分钟车程。母亲独居的老旧小区没有电梯,救护车即使到了还要爬六楼。
"患者家属您好,救护车遇到早高峰拥堵,目前还在建设路高架桥上。"调度员的声音再次响起,这次终于有了点人味,"我们已经联系交警协助开路。"
我看了眼手表——上午9:37。母亲第一通求救电话是8:25打来的。52分钟过去了,救护车还在三公里外的高架上。
"师傅,能再快点吗?"
司机无奈地摇头:"前面事故,完全堵死了。"
我摇下车窗,看到高架桥上确实停着一辆闪着灯的救护车,被卡在车流中动弹不得。那会不会就是派往我母亲那里的?这个念头让我胃部绞痛。
手机突然传来一声闷响,然后是长久的静默。
"妈?妈!"
没有回应。只有电视机里传来某档综艺节目的笑声,荒诞得令人窒息。
9:48,我终于冲进小区。楼下停着两辆警用摩托车,却没有救护车的踪影。我一步三个台阶地往上冲,心脏快要跳出胸腔。
推开门的那一刻,我看到母亲倒在沙发旁,一只手还伸向电话座机。她的脸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灰白色,嘴唇发紫。我跪在地上,颤抖着去探她的脉搏。
没有。什么也没有。
"妈..."我轻轻摇晃她的肩膀,仿佛她只是睡着了,"救护车马上就来了,你再坚持一下..."
门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担架车轮的响动。三个穿白大褂的人冲进来,为首的医生只看了一眼就摇了摇头。
"死亡时间,上午9:50。初步判断是急性心肌梗死。"医生摘下听诊器,"很遗憾,我们尽力了。"
我盯着他们胸前的标识——仁和医院急救中心。这不是最近的医院。最近的市立中心医院只有三公里,而仁和在八公里外。
"为什么是你们?市立医院的救护车呢?"我的声音平静得可怕。
医生和护士交换了一个眼神。"调度中心分配的,我们接到任务就立刻赶来了。"医生顿了顿,"路上确实很堵。"
我看向墙上的挂钟——从母亲第一通求救电话到现在,整整85分钟。
后来警方告诉我,母亲很可能在拨打120后半小时内就已经心脏骤停。即使救护车准时到达,生还几率也不足30%。但他们不知道,这个"即使"对我而言有多残忍。
在太平间签完一堆文件后,我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,盯着手机里和母亲的最后一张合影。那是上个月她生日时拍的,她穿着那件穿了十年的藏青色毛衣,对着镜头比了个老土的剪刀手。
一个穿白大褂的女医生在我旁边坐下,递来一杯热水。"我是苏晴,心内科医生。"她的声音很轻,"刚才看了您母亲的病历,她有明确冠心病史,去年体检就提示过风险。"
我抬头看她,苏晴约莫三十出头,眉眼间透着疲惫,但眼神很干净。
"如果及时送医,有救吗?"
苏晴抿了抿嘴唇:"急性心梗的黄金抢救时间是发病后120分钟内。越早开通血管,存活率越高。"她停顿了一下,"您母亲从发病到...差不多90分钟。理论上,来得及。"
这句话像一把刀插进我的心脏。理论上。
"为什么救护车要一个半小时才到?"
苏晴望向走廊尽头,那里有几个医护人员正在说笑。"这个问题,您可能得问调度中心。"她站起身,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,"如果需要帮助,可以找我。我父亲...三年前也是类似情况。"
我看着名片上"苏晴 主治医师"几个字,突然明白了她眼中的那份理解从何而来。
离开医院时,天已经黑了。我站在公交站台,看着一辆120救护车呼啸而过,警笛声刺破夜空。它开往哪个家庭?会准时到达吗?还是又会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,在漫长的等待中失去至亲?
回到家,我打开电脑,搜索"120救护车响应时间"。国家标准是城市地区15分钟内,而本市去年的平均响应时间是23分钟。母亲的85分钟,显然是个极端的例外。
但真的是例外吗?在某个医疗论坛里,我看到了几十条类似的抱怨:"等了40分钟救护车还没来""父亲中风,救护车迷路了""120说没车可派"...
凌晨两点,我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,名字就叫"120永远迟到"。发布的第一条内容是:"今天,我母亲因为救护车迟到85分钟而去世。我想知道,这个城市还有多少这样的悲剧?"
配图是母亲空荡荡的摇椅,扶手上还搭着她没织完的毛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