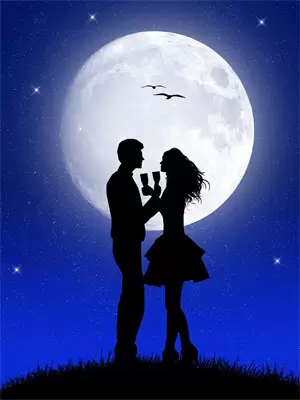
苏晚十七岁那年的夏天,是被雨水泡透的。梅雨季的雨下得绵密,
青瓦白墙的老巷里总飘着潮湿的霉味。她蹲在画室门口的石阶上,
看着江叙然蹲在积水里修她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。
少年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衬衫,裤脚卷到膝盖,露出的小腿溅了不少泥点,
却一点没影响他专注的神情——他总这样,做什么事都像在解一道复杂的数学题,
认真得让人心里发暖。“好了。”江叙然直起身,用手背抹了把额角的汗,
自行车铃被他拨得叮铃响,“试试?”苏晚跳上去,车链果然不卡了。
她蹬着车在巷子里转了个圈,雨丝扑在脸上,带着夏末特有的凉意。江叙然站在原地笑,
白衬衫被风吹得鼓起,像只蓄势待发的鸟。那是他们一起度过的第十五个夏天。
苏晚三岁搬来老巷时,江叙然是第一个跟她说话的人。那天她抱着半块融化的绿豆冰,
跌跌撞撞闯进隔壁的院子,看见他蹲在葡萄架下看蚂蚁搬家。他抬头看她,
黑亮的眼睛像浸在水里的墨石,伸手接过她快掉的冰棒:“我妈说,女孩子吃冰要慢点。
”后来的十几年里,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头禅。小学时他替她背沉重的画板,
初中时在她被男生堵在校门口时把她护在身后,高中时偷偷在她画夹里塞小纸条,
上面写着“数学公式抄三遍,放学我检查”。巷子里的街坊都笑,
说江叙然是苏晚的“小尾巴”,甩都甩不掉。苏晚的画室在老巷深处,是间带阁楼的老房子,
墙皮斑驳,却被她挂满了画。江叙然总说这里像个秘密基地,每次来都要先敲三下门,
等她应了“进来”,才推门进来,手里多半提着东西——可能是刚出炉的梅花糕,
可能是她落在学校的素描本,也可能只是一袋洗干净的草莓。“明天联考,紧张吗?
”十八岁的夏夜,江叙然坐在画室的地板上,看她对着石膏像发呆。月光从木窗棂漏进来,
在他睫毛上投下细碎的影。苏晚咬着铅笔头摇头:“有你给我划的重点,怕什么。
”她转头看他,“你真的要报本地的大学?明明可以去更好的城市。
”江叙然指尖摩挲着她画废的纸团,声音很轻:“你一个人在这里,我不放心。
”苏晚的心像被羽毛扫过,痒得厉害,却又说不出什么。她习惯了他的“不放心”,
就像习惯了画素描时先勾勒轮廓,习惯了喝奶茶时先把珍珠吸光。
她以为这就是爱情该有的样子——平淡,安稳,像老巷里的时光,走得慢,却不会迷路。
直到收到A大美术系录取通知书的那天,她在新生报到处,撞进了一双含笑的眼睛。
迎新晚会的后台挤得像沙丁鱼罐头。苏晚抱着刚画好的舞台背景板,被人群推得一个趔趄,
手里的颜料盘“啪”地摔在地上,靛蓝色的颜料溅到一双白色帆布鞋上。“抱歉!
我不是故意的!”她慌忙去捡碎片,手腕却被人轻轻扣住。“别动,小心扎手。”声音低沉,
像大提琴的最低音。苏晚抬头,撞进一双含笑的眼睛里。男生穿着简单的白T恤,牛仔裤,
鼻梁上架着细框眼镜,镜片后的目光温和又清晰。他蹲下来,用纸巾擦掉她手背上沾的颜料,
动作自然得像认识了很久。“我叫周砚礼,音乐系的。”他指了指被弄脏的鞋子,笑了笑,
“看来这双鞋跟你有缘,得留着纪念。”苏晚的脸一下子红了。她后来才知道,
周砚礼是学校的风云人物,钢琴弹得极好,却总爱穿洗得发白的T恤,
抱着吉他坐在湖边的长椅上唱歌。有人说他是音乐系的天才,也有人说他性格孤僻,
可苏晚每次见到他,都觉得他眼里有光——不是耀眼的那种,是像月光一样,
安静地淌在眼底。他们的第二次见面,是在图书馆的画册区。
苏晚踮着脚够最高一层的《莫奈全集》,周砚礼恰好从旁边经过,伸手就取了下来。
“喜欢印象派?”他翻到《睡莲》那一页,“莫奈的光影里藏着夏天。”苏晚点头,
看着他指尖划过画册上的色彩:“我总抓不住那种流动的感觉。”“试试在阳光下画吧,
”他侧过头,阳光透过窗户落在他睫毛上,“光会告诉你答案。”那天下午,
周砚礼教她辨认不同时段的光线色温,她给他讲油画颜料的调配比例。
他知道她画不出满意的作品时会咬嘴唇,知道她喝咖啡要加两块方糖,
知道她喜欢在画累了的时候去操场看晚霞。这些细微的懂得,是江叙然从未给过的。
江叙然会在她画到深夜时送来热牛奶,会在她抱怨画不好时说“没关系下次努力”,
却从不会问她“你是不是觉得阴影的层次少了一点”。苏晚开始期待每周三下午的油画课,
因为周砚礼总会坐在她斜后方的位置。他画画时很安静,只偶尔转笔,
笔杆敲在画板上的声音像节拍器。有一次她画得太投入,
不小心把红色颜料蹭到了他的白T恤上,他却笑着说:“正好,这抹红比纯色好看。
”她开始在画本上偷偷画他。画他弹钢琴时微微前倾的肩膀,画他低头调吉他弦时的侧脸,
画他坐在湖边看晚霞时,被风吹起的衣角。那些画里的线条,带着她自己都没察觉的温柔。
江叙然是在一个周五的下午察觉到变化的。他按惯例买了奶茶去苏晚的宿舍楼下等,
却看到她和周砚礼一起从图书馆走出来。周砚礼手里拿着她的画板,她低着头笑,
刘海被风吹到额前,周砚礼伸手替她拨开了。那一瞬间,江叙然手里的奶茶差点没拿稳。
他站在香樟树下,看着他们并肩走远,苏晚的笑声像碎掉的星星,一点点落进他心里,
却带着刺。江叙然开始更频繁地出现在苏晚的生活里。他会算好她没课的时间,
拉着她去逛老书店;会在她和周砚礼约好去看画展时,突然说“我妈做了你爱吃的糖醋排骨,
必须回家吃”;会在她画周砚礼的素描时,不动声色地把画纸抽走:“别画别人,画我。
”苏晚感到了压力。她试图跟江叙然解释:“我和周砚礼只是朋友。”“朋友会替你拨头发?
朋友会记得你喝咖啡要加两块糖?”江叙然的声音带着她从未听过的急躁,“苏晚,
你看着我的眼睛说,你对他没别的想法?”苏晚避开他的目光。她不敢说,
自己会在画周砚礼弹钢琴的侧影时心跳加速;不敢说,听到他在湖边唱自己写的歌时,
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;不敢说,她开始期待每天早上打开手机,看到他发来的“早安,
今天适合画晨光”。那个周末,苏晚和周砚礼去郊外写生。秋日的阳光穿过树林,
在画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周砚礼突然停下画笔,问她:“你那个发小,是不是喜欢你?
”苏晚的笔顿了一下:“我们从小一起长大,他对我一直很好。”“好和喜欢不一样。
”周砚礼看着她,“就像你画我时,眼神里的光,和画风景时不一样。
”苏晚的心跳漏了一拍。她想起江叙然在老巷里说的“我守着你”,
想起周砚礼说的“光会告诉你答案”,突然觉得,自己好像站在两条路的岔口,
一条通向熟悉的旧巷,一条通往未知的远方。变故发生在十月末。
苏晚的油画作品入选了全国大学生画展,需要去北京参加开幕式。她给江叙然打电话,
想告诉他这个消息,电话那头却传来他妈妈焦急的声音:“晚晚,叙然出车祸了,
现在在医院!”苏晚赶到医院时,江叙然刚从手术室出来,腿上缠满了绷带。他看到她,
扯了扯嘴角:“别担心,小伤。”“怎么回事?”苏晚的声音在发抖。
他妈妈叹了口气:“为了给你买限量版的颜料,骑电动车赶去美术用品店,
被闯红灯的汽车撞了……”苏晚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。她看着江叙然苍白的脸,
突然想起小时候,他为了帮她抢回被抢走的画笔,被高年级的男生推倒在泥地里,
却还笑着说“没事”。
那些从小到大的画面像电影一样在眼前闪过:暴雨天他背着她蹚过水洼,
停电的夜晚他举着蜡烛陪她画画,高考前他把整理好的笔记塞给她,说“你只管画画,
其他的我来”。那天晚上,她在病房外的走廊坐了很久。
周砚礼发来消息:“北京的票我帮你订好了,我陪你去。”苏晚回了三个字:“谢谢你。
”然后关掉了手机。她知道,自己必须做出选择了。江叙然住院的日子里,
苏晚每天都去陪他。她给他读画册,给他削苹果,给他讲学校里的趣事,绝口不提周砚礼,
也绝口不提画展。江叙然看出了她的犹豫。某个下午,他让她扶着自己在病房里慢慢走,
突然说:“晚晚,你是不是想去北京?”苏晚的脚步顿住了。“我知道你喜欢画画,
”他低头看着自己打着石膏的腿,声音有些涩,“那个画展对你很重要。
”“可是你……”“我有我妈照顾,没事的。”他打断她,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,
像小时候一样,“去吧,别让自己后悔。”苏晚的眼泪突然掉了下来。她知道,
江叙然总是这样,永远把她的愿望放在第一位,哪怕自己受委屈。可这份沉甸甸的好,
让她越来越喘不过气。她想起上周去画室拿东西,看到江叙然在她的画架上贴了张便利贴,
上面写着“记得给画布刷底料,你总忘”;想起他住院前一天,还在微信里叮嘱她“降温了,
别穿短裤”。这些细密的关心像一张网,把她裹在中间,温暖,却也让她窒息。
去北京的前一天,苏晚去画室收拾东西。周砚礼等在画室门口,手里拿着一个画框。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