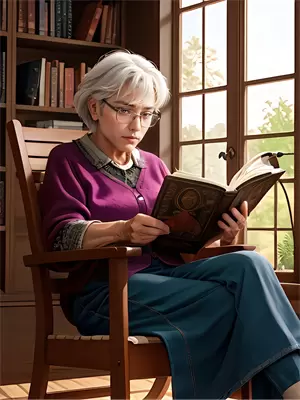1 潮音里的祈愿渤海湾的风总带着股咸涩的劲儿,刮过龙王庙前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时,
能转出呜咽似的响。槐树下住着老两口,男的叫王海柱,女的唤作李秀娥,
守着三间漏风的海草房,在这儿住了快五十年。天还没亮透,王海柱就踩着露水往海边去。
他那双胶鞋的鞋底补过七回,鞋帮上沾着的海泥结了层硬壳,走在鹅卵石滩上,
发出咯吱咯吱的响。渔网搭在胳膊上,网眼儿里还缠着去年的海菜,灰扑扑的,
像团揉皱的旧布。“今儿个要是再空网,锅里可就见底了。” 李秀娥的声音从身后追过来,
带着点颤。她倚在门框上,蓝布褂子的肘部磨出了透亮的窟窿,鬓角的白发被风撩得乱晃。
王海柱没回头,只闷闷地应了声:“知道。”他这一辈子,就没跟大海红过脸。
年轻时能凭着一口气潜到三丈深的海底摸海参,可如今腰背早就弯成了虾米,
撒网时得先蹲下来攒攒劲儿,再猛地往后一仰,渔网才能勉强撑开个像样的弧度。
潮水退了半尺,滩涂上留着密密麻麻的蟹爪印。王海柱选了块礁石蹲坐,
望着灰蒙蒙的海面发怔。他想起三十年前,李秀娥刚嫁过来时,总爱坐在这礁石上织网,
辫梢上别着朵小雏菊,笑起来眼睛弯得像月牙。那会儿他们总说,等攒够了钱,就盖瓦房,
生三个娃,大儿子随他出海,二丫头跟秀娥学织网,小儿子送镇上念书。
可老天爷偏不遂人愿。秀娥怀过三回,都没留住。最后那次在镇卫生院,
大夫摇着头说:“王大哥,大嫂这身子骨,怕是难了。” 那天回家,
秀娥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整整一夜,第二天眼睛肿得像桃儿,却笑着对他说:“柱子,
咱没娃,就俩人好好过,也挺好。”这话骗了他,也骗了她自己。去年秋里,
他起夜时撞见秀娥对着月光抹泪,手里攥着块小布片,是她年轻时绣的虎头鞋样子,
针脚都磨平了。“哗啦啦 ——” 渔网落水的声音惊飞了礁石上的海鸟。
王海柱盯着那片起伏的浪,心里头像揣着块铅。第一网拉上来时,网兜里只有几根海菜,
绿莹莹的,挂着晶莹的水珠,看着倒新鲜,可填不饱肚子。他把海菜摘下来塞进竹篮,
这东西晒成干,掺着玉米面还能熬顿糊糊。第二网撒下去时,风突然紧了。
乌云从天边压过来,海面上翻起灰黑色的浪,像一锅煮沸的墨汁。王海柱心里咯噔一下,
这天气怕是要变。他正想收网回家,却见渔网坠在水里的地方,突然鼓起个小小的浪头,
一下下撞着网面,像是有活物在里头扑腾。“难道是条大鱼?” 他心里一动,
攥着网绳的手紧了紧。往年这时候,偶尔能网到尺把长的鲈鱼,能换半袋糙米。
他深吸一口气,弓起后背使劲往上拽。网绳勒得手心生疼,水里的东西却纹丝不动。
王海柱憋得脸红脖子粗,忽然脚下一滑,整个人往前踉跄了两步,网绳猛地一松,
紧接着又被狠狠往下拽 —— 那东西发力了!“好家伙!” 他咬着牙,
把绳头缠在胳膊上,用尽全身力气往后仰。海浪拍打着礁石,溅了他满脸咸水,
他却顾不上擦,眼睛死死盯着水面。渔网一点点往上冒,网眼儿里挂着的水珠在风里飞散,
像撒了把碎银子。当网口露出水面时,王海柱愣住了。网里裹着条红鲤鱼,足有二尺长,
通身的鳞片红得像团火,在灰蒙蒙的天光下闪着奇异的光泽。最奇的是它的眼睛,圆溜溜的,
竟像是蒙着层水汽,望着他时,那眼神里竟带着点…… 哀求?他把渔网拖到礁石上,
蹲下来仔细看。这鱼的鳞片比铜钱还大,边缘泛着金边,鱼尾摆动时,能甩出细碎的虹光。
王海柱打了一辈子鱼,从没见过这样的宝贝。“这要是卖去城里的酒楼,少说能换两石米,
还能给秀娥抓副好药。” 他咽了口唾沫,伸手想去摘鱼。可指尖刚碰到鱼鳞,
那鱼突然猛地一挣,眼睛里竟滚下两颗水珠,顺着鳞片滑进网兜里,洇出小小的湿痕。
王海柱的手僵住了。他想起秀娥常说的话:“万物有灵,咱不能为了口吃食,作践了性命。
” 那年冬天,她见着只冻僵的野狗,愣是把家里仅存的半块窝头掰了一半喂它,
自己饿了两顿。风更急了,浪头拍在礁石上,碎成白茫茫的一片。红鲤鱼不再挣扎,
就那么静静地望着他,眼睛里的水汽越来越重,像是有流不完的泪。“唉。
” 王海柱叹了口气,松开了手。他想起锅里的米缸,想起秀娥咳嗽时捂着胸口的样子,
心里像被针扎似的疼。可再看看这条鱼,那通人性的模样,实在下不去手。“罢了罢了,
” 他解开渔网的活结,“你走吧。咱穷是穷,可也不能做亏心事。”红鲤鱼被放进水里时,
并没有立刻游走。它在王海柱脚边转了三圈,尾巴轻轻拍打着水面,像是在作揖。
然后猛地摆尾,化作一道红光,钻进了翻涌的浪涛里,眨眼就没了踪影。
王海柱望着空荡荡的海面,心里头空落落的。他扛起空渔网,竹篮里的海菜晃悠着,
像在嘲笑他的傻。回家的路上,风卷着沙粒打在脸上,生疼。他不知道该怎么跟秀娥说,
也不知道今晚的晚饭该怎么办。2 空缸里的奇迹海草房的门是用旧木板拼的,关不严实,
风一吹就吱呀作响。李秀娥正坐在灶门前添柴,见他回来,赶紧站起身,
眼睛在他身上扫了一圈,落在空落落的渔网上时,眼神暗了暗,却还是笑着说:“回来啦?
我去烧点热水。”王海柱把渔网扔在墙角,蹲在门槛上,吧嗒吧嗒地抽起旱烟。
烟杆是用枣木做的,被他叼了十几年,磨得油光锃亮。“秀娥,” 他闷闷地开口,
“今儿个…… 网着条红鲤鱼,挺大的,我给放了。”李秀娥添柴的手顿了顿,没回头,
只轻声问:“是条好鱼吧?”“嗯,红得像火,鳞片还闪光,看着就不一般。”“放得对。
” 她把柴塞进灶膛,火苗 “腾” 地窜起来,映得她的脸暖暖的,“那样的鱼,
怕是通灵性的。咱穷点没事,别坏了良心。”王海柱抬起头,看着她的背影,眼眶有点热。
这辈子,他最庆幸的就是娶了这个女人。晚饭是海菜糊糊,稀得能照见人影。
李秀娥把碗里仅有的几粒米都拨到他碗里,自己就着咸菜喝了两口,说:“我不饿。”夜里,
王海柱被冻醒了。身边的秀娥睡得不安稳,时不时咳嗽两声,眉头皱得紧紧的。
他摸了摸她的额头,有点发烫。他想起来,上个月镇上的郎中说,秀娥这是风寒入了肺,
得抓几副药调理,可他那会儿连买米的钱都没有。窗外的风还在吼,像有无数头野兽在嚎叫。
王海柱睁着眼睛望着黑乎乎的房梁,心里头堵得慌。他这辈子没求过人,可现在,
他真想对着老天爷磕几个头,求它发发慈悲,别让秀娥再遭罪了。第二天一早,
王海柱是被饿醒的。他摸黑爬起来,想去外屋看看还有没有剩下的糊糊。
外屋是灶台和米缸所在的地方,借着从门缝透进来的微光,他看见米缸的盖子好像没盖严,
露出条缝。“怪了,昨晚我明明盖紧了。” 他嘟囔着走过去,伸手掀开盖子。这一掀,
他整个人都僵住了。米缸里满满当当的,全是白花花的大米,颗颗饱满,还带着股清香味儿。
他揉了揉眼睛,以为是饿花了眼,伸手抓了一把,米粒在掌心凉凉的、滑滑的,是真的!
“秀娥!秀娥!你快来看!” 他声音都抖了。李秀娥披着衣服跑出来,看到米缸时,
也惊呆了。“这…… 这是咋回事?”两人正愣着,王海柱又发现了新东西。
灶台旁边的木板上,摆着一串腊肉,油光锃亮的,还冒着点热气;墙角堆着半筐鸡蛋,
个个圆滚滚的;甚至还有一小坛酒,泥封得严严实实。“这是谁送的?” 李秀娥喃喃地说,
“咱也没亲戚啊。”王海柱蹲下来,摸了摸地上的水渍。外屋的泥地是夯实的,
平时洒点水很快就干,可现在这水渍却连成了片,还带着点淡淡的海腥味。
他抬头看了看屋顶,茅草铺得好好的,没漏雨。“甭管是谁送的,先给你熬点粥。
” 王海柱反应过来,赶紧生火,“你发着烧呢,得吃点好的。”米粥熬得黏糊糊的,
李秀娥就着鸡蛋吃了小半碗,脸色好看了不少。王海柱啃着腊肉,
心里却犯嘀咕:这事儿太邪门了。接下来的几天,天天如此。每天早上,
外屋都会凭空多出些东西,有时是新鲜的海鱼,有时是雪白的面粉,甚至有一次,
还出现了块花布,料子细腻,正是秀娥年轻时最喜欢的那种。老两口心里又惊又喜,
却也越来越不安。这天晚上,王海柱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,说:“秀娥,今晚咱不睡,
看看是谁在帮咱。”李秀娥点点头:“我也睡不着,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”两人熄了灯,
躺在床上装睡。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棂照进来,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风停了,
只有海浪拍岸的声音,一下下,像打更的鼓。一更天过了,没动静。二更天过了,
还是没动静。就在两人快要撑不住时,突然听到外屋的门 “吱呀” 一声开了。
王海柱屏住呼吸,轻轻推了推李秀娥。两人蹑手蹑脚地走到里屋门口,从门缝往外看。
月光下,一个小小的身影正在灶台前忙活。那是个男孩,看着约莫七八岁的样子,
穿着件红肚兜,皮肤白得像玉,头发黑亮亮的,梳着两个总角。他正踮着脚,往米缸里倒米,
嘴里还嘟囔着:“昨天的鱼好像没吃多少,是不是不合胃口?明天换条鲈鱼试试。
”他的声音脆生生的,像浸了蜜的铃铛。王海柱和李秀娥对视一眼,
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惊讶。男孩倒完米,又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,打开一看,
是几块精致的糕点,他小心翼翼地摆在盘子里,又自言自语:“娘咳嗽还没好,
这桂花糕润肺,应该爱吃。”“娘?” 李秀娥捂住了嘴,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。
王海柱深吸一口气,猛地推开门:“你是谁家的娃?”男孩吓了一跳,手里的糕点掉在地上。
他转过身,看到王海柱和李秀娥,眼睛瞪得圆圆的,像受惊的小鹿。
“爹…… 娘……” 他迟疑着,小声喊了一句。“你叫俺啥?” 王海柱愣住了。
男孩 “扑通” 一声跪下了,磕了个响头:“爹,娘,我是你们放的那条红鲤鱼啊。